陳映真文學的時代意義:一個中國式的視角|趙剛
在陳映真逝世一周年,以及他的23卷全集甫出版的今天,「為何紀念陳映真?」已經不是問題了,而今後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紀念陳映真?」這篇短文是作者對那個應該過期的問題的最後一次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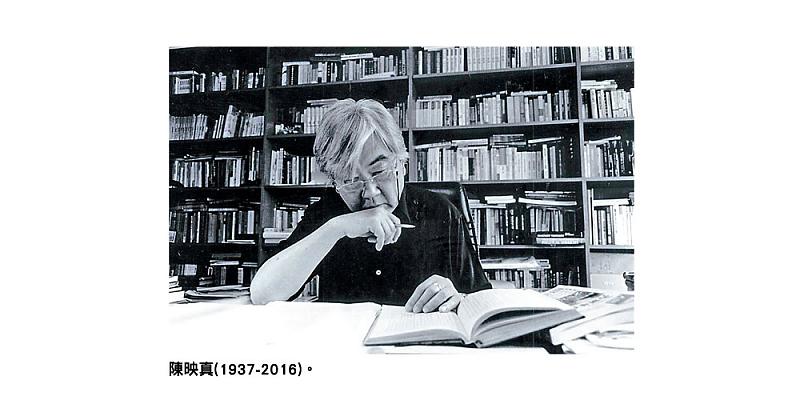
陳映真文學是魯迅、是五四,也同時是一種中國傳統文學觀,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孤獨」並非修辭,而是一個歷史事實的描述。我們只需以這樣的一個提問,即可回答:在戰後台灣的這半個多世紀以來,除了陳映真,能找出第二個如此嚴肅面對文學的道德性、時代性、思想性,與政治性的文學創作者嗎?這麼提問,也意味著台灣當代的文學及藝術,一般而言,是與魯迅傳統的切斷,也是與五四傳統的切斷,更也是與一種中國傳統的切斷。這個「切斷」,用陳映真的表述方式,就是「現代主義」的問題;於是長期以來,陳映真以「現實主義」為旗幟和「現代主義」鏖戰。但是,我們不應把這個戰鬥狹義地理解為一場「文學領域」的戰鬥,而要以更廣闊、更「暗喻」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戰鬥。
孤獨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
「現代主義」遠遠不只是一種文藝的表現形式而已,而是關於人生、社會,以及世界該當如何的一種表述與一種宣示。因此,陳映真以「現代主義」為「名對象」的戰鬥,並不是閉鎖於文學領域之內的爭論,而是關於「什麼才是人生?怎樣才是活著?」的鬥爭。陳映真碰巧只是以他所熟悉的文學路徑,進行這場鬥爭而已。因此,不止一次,他說,重要的是找到生存的目標,並為之而思想與奮鬥─「人不一定非要寫作」。
陳映真對文學本身的「看輕」,反而使他的文學有了無比的重。文學要到哪兒去,這個「道」的問題,以及需要什麼能力修養以達到目的的「德」的問題,於是成了內在於文學的重要問題。對「如今,文學還需要和道/德掛勾嗎?」這樣的質疑,陳映真以他的文論,以及更重要的文學,現身說法開展出他的否定。
從一種中國傳統視野出發,文學和道/德之間的關係是深刻而內在的。在以下的篇幅裡,我將借用這個「三達德」為架構,說明陳映真文學和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同時也順道落實之前所提出的,陳映真是一個偉大文學傳統在當代台灣的孤獨繼承的論斷。
對人間布滿同情共感
首先,「仁」。陳映真文學到處布滿了對於「人間」同情共感的脈搏與神經。誠然,沒有一種文學只是在書寫作者自身的內在,哪怕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會與歷史。陳映真總是能痛苦而豐富地感受到人間各個階層、各個旮旯的人物群像,特別是那不為我們體面社會的紳士淑女所參與、所瞭解、所同情的那「後街」眾生。
於是,我們讀到了台灣資本主義裡最早出現的底層城鄉移民的貧困與無奈、讀到了小知識分子的苦悶徬徨虛無與自責、讀到了失根流落傷逝的外省老兵、讀到了台灣左翼抗日知識分子矇朧而執著的中國認同與情懷、讀到了青年精神病患似幻似真的輕與重、讀到了日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虛無敗德的「上層社會」、讀到了都會摩登知識分子的「表演」、讀到了越戰時期來台「性度假」的美國黑人大兵與台籍農家女子之間的跨越膚色與國界的愛情及其幻滅、讀到了跨國公司的內部帝國與殖民、讀到了1950年的白色恐怖、讀到了國民黨特務的良心。
這些,都和技巧無關,甚至和所謂文學無關,歸根究底,和陳映真盎然的、沛然的對他人的感受力有關。讀陳映真文學的一個最豐厚的回報,或許就是讓讀者從而產生自我提問:那我又將如何培養這種感受力呢?
總在思想時代問題
其次,「智」。陳映真文學的一大特徵就是總是在思想著,儘管不見得有解答。陳映真每一篇小說都是在處理他所深自關心或困擾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最後是收束在一個道德性,甚至是宗教性的問題上:「究竟人該當如何活著?」但他回答問題的方式並不是形上學的,而是透過歷史與現實。
50年陳映真文學曾經認真思索過的問題包括: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的遺留;冷戰、分斷與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精神創傷;第三世界新舊殖民體制下的知識狀態;跨國資本主義對於在地人民的主體創傷與社會扭曲;左翼的道德主體狀態的危機及「女性問題」;宗教在當代的意義;當理想遭遇重大危機時,主體該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跳出無盡的加害與受害的循環?
於是,陳映真文學的「智」,不只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世界,與他人進行外在的體察,更是一種內在的「明」。古人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貫穿陳映真文學整體的是一種深刻的自省力,以及一種類似懺悔錄的「把自身包括進來的」書寫,而我相信這正是他在「知性」上最光輝的展現,而我們不要忘記,這也是來自於魯迅的傳統。
我們是會執著地問:對照於陳映真長期的、不間斷的「困而知之」的思想實踐,這個島嶼上有類似的同行者嗎?但對我們讀者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閱讀陳映真是否讓我們自我提問:我要如何自知?
用寫作向現代霸權戰鬥
其次,「勇」。作為知名小說家,陳映真最常被誤解的是他的論文是戰鬥的,而小說則是「感性的」、「人道的」。但我要說,他的所有寫作都是他的戰鬥。他首先是一個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而非倒過來。台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寫作的最大的「故意盲點」,其實就是對陳映真戰士資格的否定或嘲笑,而這恰恰是因為陳映真的戰鬥,都朝向他們及其背後的現代霸權戰鬥。
獨派對陳映真的無視或否定其實本身就是一種戰術,不過是比較鬼祟暗欺罷了。他們以台獨霸權否定陳映真寫作後期裡「民族統一」的戰鬥,以「現代主義」大而化之,顛而倒之陳映真寫作前期的「反現代主義」戰鬥。但其實,陳映真文學是不分前後期的,只因打從一開始,他就是站在一個中國人的、左翼的、第三世界的、理想主義的位置而寫作。這是他一生的戰鬥,而他為這個戰鬥付出的代價,包括蔣介石政權下的七年牢獄,以及台獨霸權下的不定期圍剿與刻意遺忘。然而,陳映真自反而直,不改其志─這是他的大勇。
陳映真的各項「首先」
因此,人們不應當隨著獨派的「台灣文學史」催眠,而遺忘了這個戰士所歷經的各個大小「戰役」。於是,我要指出陳映真文學在當代台灣文學史中的各項「首先」。
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麵攤〉(1959),檢討了台灣初生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鄉移民與貧困議題。是陳映真,首先透過〈鄉村的教師〉(1960),探討了一個左翼志士的生與死,以及他所經歷的日本殖民統治、太平洋戰爭、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展開的白色恐怖。是陳映真,透過〈將軍族〉(1964),首先探討了所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是陳映真,透過〈一綠色之候鳥〉(1964),首先批判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改革希望」。是陳映真,透過〈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首先批判了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越南戰爭。是陳映真,透過了〈唐倩的喜劇〉(1967)等多篇小說,首先面對了國府統治下「西化」知識分子的某種閹割與失根狀態。是陳映真,透過〈夜行貨車〉(1978),首先批判了跨國資本主義對於第三世界的宰制與扭曲效果。是陳映真,透過〈纍纍〉(1979),首先直接以批判指出那些當年被抓伕來台的底層外省軍官的寂天寞地。是陳映真,以〈鈴鐺花〉(1983)等小說,首先檢視與反省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的傷害與變形。
這些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眾多「首先」,卻無奈地一直被此間「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者視而不見,反而在「研究」陳映真文學,算不算是「現代主義文學」。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無法交待自己在那個年代中的葸弱無能,而那勇敢戰士竟是一個所謂的「統派的」「中國人」嗎?在戒嚴體制下苟全人生,是人情之常,無可批評,但我們不應因今日的意識形態分歧,而塗銷或扭曲勇者畫像。在台灣1960年以降的「文學領域」裡,找得到第二位像陳映真這樣的戰士嗎?
(作者係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趙剛
- pages: 72
- 標題: 陳映真文學的時代意義:一個中國式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