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鈴璫花〉,向陳映真致贊禮|古添洪
〈鈴璫花〉是陳映真對白色恐怖左翼菁英的緬懷。這鄉土小説以童年往事為通體架構,以代表當時愛國主義與樸素社會主義的高老師為主脈。鈴璫花的象徵,把小説的境界提高到宇宙生命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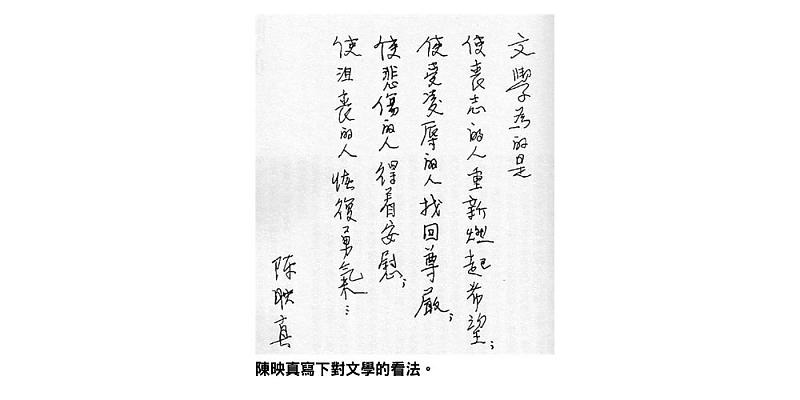
陳映真於1960年代參與讀書會,親近社會主義,因而繫獄。六年多的牢獄歲月,卻使他更加堅定,終身為其理想而奮鬥。陳映真對他的前代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裡,為民族統一和社會主義事業而犧牲的菁英,應該是心有之所繫的吧!然而,直到1980年代初,才對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用文學之筆寫下他的緬懷。〈鈴璫花〉就是這緬懷系列的首篇。
〈鈴璫花〉的鄉土味很濃,可說是道地的鄉土文學。陳映真把故事的場景放在他童年成長的故鄉鶯鎮(即鶯歌),也應有著一些自傳的抒懷吧!隨著身在1980年代的敘述者莊源助的童年往事敘述,以好友阿順帶頭的探險記裡,1950年代的鶯歌歷史,鄉野與風土人情也彷彿在我們眼前復活了。
從大陸撤退的國軍寄居在松林下鶯歌國小的老教室內,食物不潔,痢疾流行,士兵往往因而死去。從南部遷來這福佬地區的客家林家,種得一地好蕃薯,大家都愛吃,被稱作「客人仔蕃薯」,可惜男人胃病死去,祗剩下寡母及閨女在勤勞耕種。身分神秘、從大陸過來的金先生,獲娶從上海回鄉的本地房東的女兒,而房東不久也就當了鎮公所的戶政科長,談著三民主義。金先生帶來的外省家庭特色,幫忙新婦下厨、洗衣服,著實引起了當地婦女的驚嘆,「外省男人怎麼跟我們的男人不同款哩!」還有日本北白川宮親王征台時在此設帳的行宮紀念碑,就荒棄在目前國軍駐營的後方。仰臥在草坡上,就可以看見傳說是鄭成功收伏鳶精的鳶山。
光復時鶯鎮的民心奮發(阿順因而得以復學),二二八事件的整肅(光復兩年後阿順的遠親失蹤),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就在高老師失蹤的那一年,「整個鶯鎮出奇的沉悒,連大人也顯得沉默而懼畏」),這些鄉土舊事與歷史糾葛,都是在這童年往事裡經由孩童的視覺與話語裡不明就裡地帶出來的。甚至是故事的主脈,自願當放牛班導師的高東茂老師的悲情故事,也是在這童年探險記裡斷續地穿梭而成。這就是陳映真寫實主義在敘述美學上的經營,所有原屬非美學的現實元素,都馴服在通體美學結構裡,轉化為感性與現實底肌理相互辯證的藝術作品。在這裡,盧卡奇(Georg Lukacs)的寫實主義獲得了進一步的印證,而陳氏悲憫情懷的底色,使到寫實帶有一份東方的神韻。
與稍前的巨作《華盛頓大樓》相較,陳映真從電影手法移向自然的敘述,事態的展開,欲斷還連,一種錯落有致的節奏感,那是敘述體難得的神韻。至於他的文字,直入實境,用鍾嶸論陶淵明詩的「文體省净」稱之,或可得之。特別的是,讀陳映真的作品,往往感受到其溫情的筆觸,卻很難加以學術的解釋。
高老師代表的是新中國初年充滿前景的積極心態,說實一點,也不外是愛國情懷與最樸素的社會主義,如此而已。然而,隨著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展開對社會主義支持者的全面肅清,其餘浪在台灣也就激化為與國土分裂有關的白色恐怖,而高老師的被盯上、出走、山洞躲匿,終而被捕、槍決,正是其中典型的例子。「高老師這麼好,為什麼不說一聲就走了呢?」阿順簡短的一句話,就道盡了那一代知識青年的高尚品格與歷史的心酸了。至於高老師在班上所表現的激勵愛國情操的教唱、反對歧視弱勢的分班、與關懷阿順的正義舉措,這裡就不再細述。
阿順與阿助的童年冒險往事,也是最鄉土的,最鶯鎮的。廢窯、秘密寶藏、私屬的樹、養青蛇、抓筍龜、偷花生、溪泳、逃學、溜進營房與士兵吃飯,加上前面提到的鄉土遺留的歷史糾葛、高老師對他們的啓蒙,以及突然發覺下體毛髮蓬鬆,幾乎是他們童年成長史詩般的表達。篇中所表達的無邪、冒險、自由、成長、以及友誼,更會勾起有類似經驗的舊世代人的記憶,也會勾起生活在都市叢林的新生代的無限嚮往。
小說結尾寫道,「唯獨高東茂老師那一雙倉皇的,憂鬱的眼睛,倒確乎是歷歷如在眼前。」如何安慰這英靈及這鄉土上歷史糾結隱藏的傷痛?「五瓣向上捲起的、淡紅色的花瓣,圍起一個嬰兒拳頭大的鈴子」,鈴璫花在林氏寡婦閨女屋舍籬笆怒放著。這象徵著英靈的精神不死,也象徵著萬物的生生不息。自然就是歸宿。這象徵把小說的境界提高到宇宙生命的高峰。這就是陳映真鄉土寫實文學的勝利。
當此間政治塵埃落定,我預想,1950年代的鶯鎮,將因〈鈴璫花〉而成為人們永恒的記憶。
後記:再讀及撰寫本文時,多希望大頭陳映真能親身帶我們去尋覓那童年往事的鶯鎮,去重訪我們心底那理想怒放的鈴璫花,可惜哲人已遠。
(作者係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教授)
附加資訊
- 作者: 古添洪
- pages: 72
- 標題: 讀〈鈴璫花〉,向陳映真致贊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