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良史莫不工文│龔忠武
中國史學不僅重於史論,也重於敍事,更重於文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知幾的《史通》、鄭樵的《通志》、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都是良史。

班彪父子推崇太史公的文采說,司馬遷敘述事情條理分明,據實指出是非對錯,行文典雅,不流於粗俗(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范曄也推崇班固的文采說,敘述事情,不褒貶毀譽,不刪減誇張,有遠視而不迷亂,詳細而得體,令讀者愛不釋卷(他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
劉知幾在《史通》中特別強調,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就是中國史學工於敘事,文史一家的典範。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發揮劉知幾的觀點,良史莫不工文,因為史實的記載,必須靠文學性語言傳播,以優美文辭寫成的史書,易於流傳久遠。《史記》、《資治通鑒》就是最佳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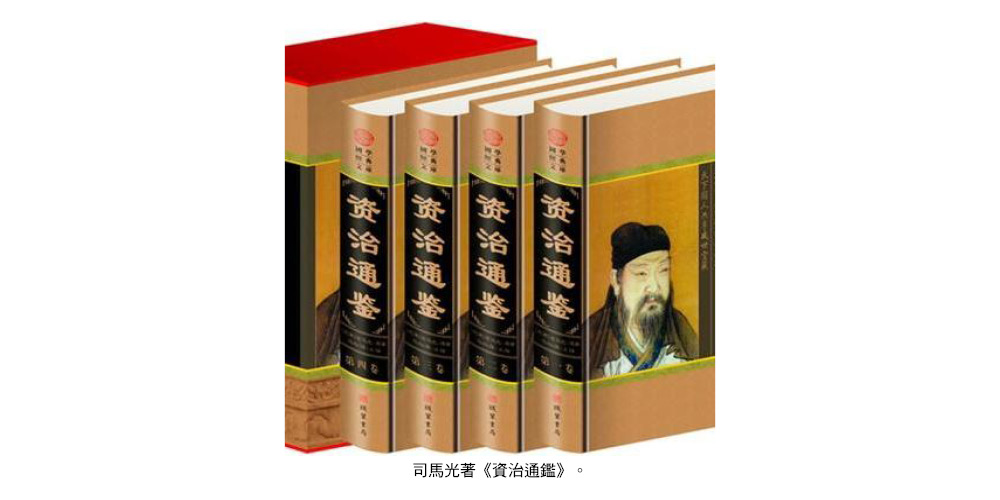
在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第八章第三節歷史文學中,引述項羽「鉅鹿之戰」的描述,以資佐證: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斧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以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這段記述生動地寫下項羽在戰場上視死如歸,英勇蓋世的霸王氣概。這就是大史家展現的文采,也即是史家莫不工文的意思。
對史學方法有深入研究的杜維運,對中國史家的敘事藝術備極推崇,認為已達到一極高的境界,審慎遣詞用字,不以文而失真,不以真而失義,文約而事豐,褒貶適中。司馬遷、司馬光樹立史家敘事之典範,劉知幾、章學誠歸納為通識、批判、懷疑、進化史觀的理論,中國史學在史論的主導下,其敘事藝術傲視世界史壇。西方史家,例如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對此也讚譽備至。
但當中國史學,在科學化的歐風美雨盛吹下,被列入社會科學後,上述中國史學優良的傳統文學性開始大為削弱,轉而強調敘事的分析性和邏輯性。未來的中國史學,如何在史學的文學性和科學性的夾縫中,找到適當的位置,是個嚴峻的挑戰。
相較於重文采的中國史學傳統,歐美傳統史學則重視一個良史,除了盡量收集充分的史料之外,不在於敘事的工與不工,有無文采,而在於敘事是否真實,以及其對史事背後的意義和教訓的解讀,例如1838年,《波士頓評論季刊》(Boston Quarterly Review),一位作者認為:歷史學家,像是一位站在瞭望塔上的觀察者,安詳地凝視著道德的蒼穹,解讀在道德的天空中發出時而光明,時而黑暗的人世現象,解答所看到的問題,解釋先知的預言,打開歷史中記載的,或源自人世經驗的寓言。
所以,西方的史學重在唐太宗所說的歷史功用:「明得失,知興衰」,沒有中國《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這樣的史書,既真實客觀,又文采斐然。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受到達爾文社會進化論的影響,西方史學更強調歷史的客觀性,盡量不要參雜個人的立場和主觀的判斷,當然更顧不上文采了,史書讀起來就更加索然無味了。加上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通篇教條式術語的堆砌,令人無法卒讀。
有鑒於此,中國史學恢復史學文采的優良傳統,兼顧史學的客觀性和文學性,已成為當代中國史家努力的目標。依筆者見,中國近代評論家、報告文學家徐遲(1914-1996),於1978年1月在《人民文學》第1期發表的,記述中國數學家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就可視為一篇傳記體的史學著作,既有史學的客觀性,又有文學的可讀性,是一篇融史學與文學為一體的佳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
附加資訊
- 作者: 龔忠武
- pages: 78
- 標題: 中國良史莫不工文




